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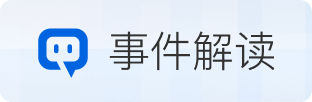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特德·姜在一次访谈中说,他现在已经不再读阿西莫夫了,虽然这的确是他早年的启蒙,也许如今还能回去读一读博尔赫斯,但不再是阿西莫夫了。他无意进一步解释,但原因显然,在其最新翻译出版的短篇集《呼气:故事》中,头两篇故事似乎一定程度解释了这种转向。
《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作为整部短篇集的开篇,指向了“故事”这个形态的隐喻,并奠定了一种文学性上的回向操作氛围。特德·姜这次模仿《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来塑形他最感兴趣的时间旅行题材。这个故事被拆分成三个叠套关联的小故事,分别是“幸运的绳匠的故事”“从自己那里偷东西的织工的故事”“妻子和她的情人的故事”。这些人物和章节都围绕着一扇可以穿越时空的门而展开,之所以采用《一千零一夜》的叙说结构,特德·姜的解释是,他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这种古老传说故事的叠套形式与时间旅行故事的递归性极为相近。同时,他又在后记中补充道:“大多数时间旅行故事都假设过去可以改变,那些无法改变过去的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尾。虽然我们都能理解改变过去的愿望,但我想尝试写一个时间旅行故事,表明无力改变过去不一定就会带来悲伤。”
这样的意愿,基本出离了阿西莫夫在《永恒的终结》中试图解决时空旅行悖论而建造的宏伟大厦。相比而言,特德·姜的创作开辟的是另一种更倾向于心灵认知范畴的写作,更关乎解脱感悟的演绎,而轻科学事实式的推想。他的时空旅行往往不提供时间线的修改方案,而是增添观看的维度。他撬动的不是过去或未来的剧情内容,而是此刻对时间线的认知。在这样一种总体性的文学建筑中,科幻元素只是他采用的某种具有高度延展性的外墙材料。
我们必须意识到,阿西莫夫和特德·姜的作品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空间。特德·姜的搭建物是轻薄的、空灵的、可移动的,几乎就类似于他小说中的门的结构。他提供的是一个引导,在这个短篇里,他尤其要将读者引向“故事”之形式本身的提示以及对它全新的认知和参与。在“妻子和她的情人的故事”那一章节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她离开以后,我在附近徘徊了好几个小时。我哭泣着,但这是解脱的哭泣。我回味着巴沙特拉的话,他说得太对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无法改变,只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我这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知道的事情却改变了一切……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安拉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那么我们既是故事的聆听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聆听和扮演人生这个故事,我们最终才能从中得到教益。”
如同《你一生的故事》一样,这部时空旅行短篇从完整的看见、共情与领会中获得解脱,意识领域的革命往往来自对自我的拆析和观看。虽然并非时空旅行题材,但这种特质也出现在《呼气:故事》的第二个短篇《呼气》中——主人公拆解了自己的机械大脑,因而发现了记忆和生命的秘密。然而这里也需要指出一个中文翻译的错误,中译本将标题“exhalation”译成“呼吸”是一种严重的转码偏差,因为在这篇小说的世界观架构中,我们的生命存在形式以及思考它的过程被发现是宇宙“呼气”的、“从稠密去向稀薄”的特指阶段:
“宇宙的开端仿佛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没人知道为什么,然而不管原因如何,我很高兴宇宙以这样的形式诞生,因为我的存在也要归因于此。我所有的欲望和沉思,都是这个宇宙缓缓呼出的气流。在这漫长的呼气结束之前,我的思维将一直存在。”
思维加速气压差,而我们所有人共享肺部和这些空气,我逐渐发现真相的过程推进了我的宇宙的解离,这样的共业系统导致了某种加速主义式的去向灭亡的阶段,但所谓灭亡的主体是什么?灭亡的指向的是什么?他写道:
“为我提供动力的空气还能驱动别人,助我刻下这些文字的空气有一天会流过别人的身体,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欣慰。我不会欺骗自己说,这是我再生的方式,因为我不是那些空气,我只是空气流动模式的体现,暂时的体现。我是一种模式,我所存在的整个世界也是一种模式,而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在阿西莫夫那里,“空气”是“在上面的循环”(《新疆域》),是殖民主义最忧心忡忡的客体,特德·姜则将空气彻底主体化了,这其实和菩萨道的思维极为贴合,甚至在小说结尾,作者企图将这种主体性回向给读者——主人公的铭文显示,他希望此刻的这位读者正是下一个如他一般的贡献者与探险者,他可能是把这个宇宙当作储气槽的其他宇宙的探险者,虽然“我们的宇宙在滑向平衡点的过程中也许只能静静地呼气”,但通过不同宇宙合力的思考与奉献,文明会不断重生,直到那一天,所有的宇宙都达到完美的寂灭平衡态。

特德·姜作品中隐秘的加速主义和菩萨道倾向,在上世纪科幻文学“新浪潮”领军人物罗杰·泽拉兹尼那里体现得更彻底。如今被左派政治哲学界借用的“加速主义”这个词,恰是来自泽拉兹尼那部怪诞的科幻玄幻长篇《光明王》,这部小说不但获得了当年的雨果奖,更是开创性地将神话与宗教哲学召回到科幻领域,并引入了诸多心理学与社会学概念,打破了当时太空冒险科幻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是上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之一。一段同样摘引自小说开篇部分的文字如此展现了这种召回,以及对那位黑塞也描绘过的人物的另一种戏解,而相比黑塞,泽拉兹尼似乎更理解佛教的世界观,尤其是推进主义的那一面:
“据说,在解脱之后的第五十三个年头,他从‘金色祥云’回到世间,再一次挑战天界,反抗诸神及其祝圣的生命秩序。他的信徒为他的回归而祷告,尽管这祷告无疑是一种罪恶——人们本不该用祈祷去烦扰涅槃之人,无论此人的涅槃是否有违自己的本意。然而,身着藏红花色僧袍的人依旧祈祷着,祈祷那手持利剑的文殊师利能够再次回到他们中间。人们都说,菩萨听到了……
彼等诸漏尽,
亦不贪饮食。
空无相解脱,
是彼所行径。
如鸟游虚空,
踪迹不可得。
——《法句经·九十三》”
这部小说里的光明王/萨姆/佛陀/弥勒/缚魔者有无数名字,他被设定为一种重叠了普罗米修斯与菩萨色彩的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t)——普罗米修斯提供了一种行为的算法,菩萨则提供了一种行为的伦理准则。这里也有一个翻译细节,中译本将“accelerationist”翻译成“推进主义者”,这个生僻的翻译反而颇为精妙,“加速”似乎会有偏向速度本身的引导,而“推进”则更指向体系加快系统自我破阈的趋向性。
光明王在小说中以开放源代码的方式,将印度教天庭垄断的先进科学技术提供给广大的人类,窃取或阴谋成为必要的手段,此举引起了天上地下的巨大混乱。菩萨被理解为一种主动放弃留在涅槃永恒中的佛,他回驻到人间,或者说回驻到这个轮回的次元之中,帮助所有有情众生,直到他们获得怔悟解脱。大乘佛教本身就是一场历史运动,它是对统治权力结构的精神储备的反应和动员,佛陀被视为一个开辟了主体性世俗化道路的人物,这种主体性不仅是对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抵制,更是揭露个体拥有全然权限的事实,通过理性而精细的思维与具身的证量,对现象世界的梦境本质进行拆析和遮破,从而获得意识领域的彻底解脱。而在泽拉兹尼的设定中,轮回和宗教概念被赋予了技术性色彩,比如祈祷机和罪恶户头,比如业报大厅、探针设备和新身体更换程序。除了佛教人物之外,数量最多的以印度教诸神命名的角色纷纷登场,各种古典神话体系被打乱,重新集结:死神阎摩和佛陀成了跨时空情敌,卡莉女神和阎摩结了场丧天丧地的大婚,喝勃艮第的梵天神秘遭刺,推进主义革命引发的诸神之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于混战中串场……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平衡的主旨贯穿整部小说,也使得它超越了一般的反乌托邦小说:
“它们开始、终结、相伴、相克,它们进入无名的梦境,附着在那梦境之上,在轮回中将语言焚烧,也许正是为了创造一点点美。而这无名,就是我们的世界。”
《星球大战》系列虽然也在类似的主题光谱中,但泽拉兹尼的大胆和功力,在于直接改写古典神话体系,而且他驾驭语言的能力令人惊叹,在如此复杂起伏的史诗级故事情节中,他的语言仍被脱俗的诗意与佛教哲学的明空智慧所护体:
“本质会梦到形式。形式消逝了,本质仍在那里,做着新的梦。人类为这些梦境命名,自认为已经摄取了本质,殊不知自己是在求助于幻境。这些石头、墙壁,这些坐在你周围的身体都不过是罂粟、水和太阳,是无名做的梦。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们叫做火。”
小说情节中光明王所代表的推进/加速主义,在这部小说的写作方法本身上得以显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将科幻写作解脱出知识型自缚的最杰出代表。随着技术发展至天人世界的阶段,这两位作者也昭示了,科幻小说完全应当是总体而灵性的。

《呼吸》
[美]特德·姜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