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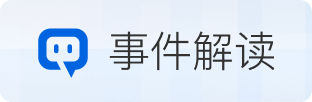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爆炸性赤字、借贷和杠杆增长之后,世界经济正在跌跌撞撞地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交汇点。
在私营部门,堆积如山的债务涵盖了家庭(如住宅抵押贷款、信用卡、车贷、学费贷和个人贷款)、各类企业(银行贷款、债券债务和私人债务)以及金融部门(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债务),而公共部门则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正式债务以及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健系统的无资金支持负债等隐性债务,所有这些都将随着社会逐渐老龄化而继续增加。
仅仅显性债务数字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在全球范围内,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总债务额相对GDP的比例已经从1999年的200%上升到2021年的350%。目前中国为330%,美国则为420%,比大萧条期间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水平都要高。
当然,如果借款人能投资于回报高于借贷成本的新资本(机械设备、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债务其实是可以提振经济活动的。但许多借款只是持续在为高于收入的消费支出提供资金——这可是破产的秘诀。此外对“资本”的投资也可能存在风险,无论借款者是以被哄抬价格购买住房的家庭、不顾回报过度扩张的企业,还是把钱花在“大白象”(奢侈但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政府。
这种过度借贷已经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持续了几十年。金融民主化使那些收入紧张的家庭能够举债消费。在央行的超宽松货币和信贷政策推动下,重债轻股的税收政策促成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借款的激增。
多年的量化宽松和信贷宽松使借贷成本一直维持在近零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负值(正如前一段时间的欧洲和日本那样)。到2020年负收益美元等值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7万亿美元,在一些北欧国家就连房屋抵押贷款的名义利率都是负的。
不可持续的债务比率暴增意味着许多借款者——家庭、企业、银行、影子银行、政府,甚至整个国家,都是资不抵债的“僵尸”,只能靠低利率撑着(这一利率使它们的偿债成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本应破产的资不抵债机构都被零/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和直接财政纾困措施救活了。
但如今,被同样一批超宽松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所推动的通胀终结了这场金融回光返照。随着各国央行被迫调高利率以恢复价格稳定,僵尸企业的偿债成本正急剧上升。对许多人来说这相当于三重打击,因为通胀还在侵蚀家庭的实际收入,并使房屋和股票等家庭资产贬值。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脆弱且过度杠杆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它们同时面临着借贷成本急升、收入和税收下降以及资产贬值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这些事态发展刚好碰上了滞胀的回归(高通胀伴随着疲软增长)。发达经济体上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但当时的负债率至少还很低。今天我们正面临滞胀冲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最糟糕一面。这回再也无法简单地通过降息来刺激需求了。
毕竟全球经济正受到持续的短期和中期负面供应冲击的打击,这些冲击正在延缓增长,推高价格和生产成本。问题包括疫情对劳动力和商品供应的干扰;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地缘政治形势发展的其他十余个可能导致额外滞胀压力的中期冲击。
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头几个月不同,简单地用宽松的宏观政策来救援私人和公共部门只会给通胀火上浇油。这意味着会在一场严重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出现一次硬着陆,即一场深度而持久的衰退。随着资产泡沫破裂,偿债比率飙升,家庭、企业和政府排除通胀因素后的收入下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将相互强化。
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利用一轮意想不到的通胀来降低一些名义长期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各国政府都不愿通过加税或削减开支来削减赤字,央行赤字货币化将再次被视为阻力最小的途径。但你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人。一旦通胀精灵走出瓶子(这将在各国央行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放弃抗击后发生),名义和实际借贷成本都将大幅上升。这个一切滞胀债务危机之母可以被推迟,但却无可避免。
(作者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版权:辛迪加)